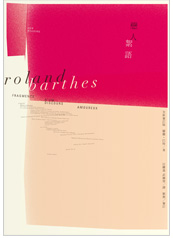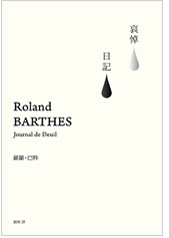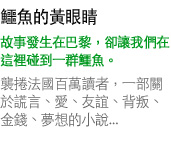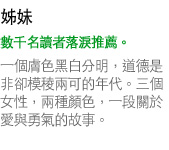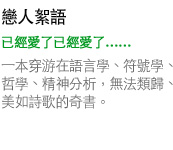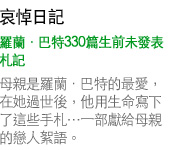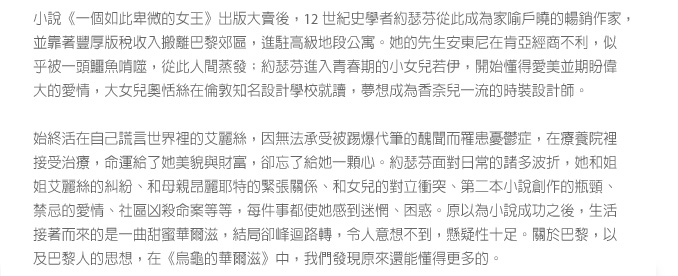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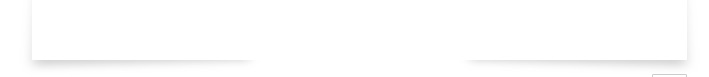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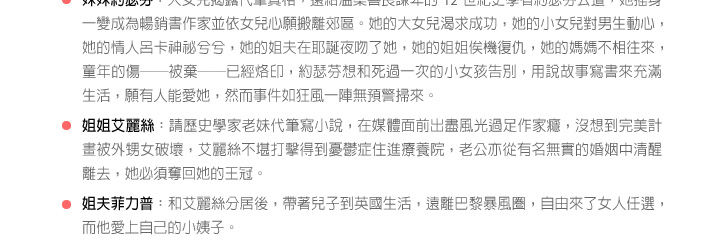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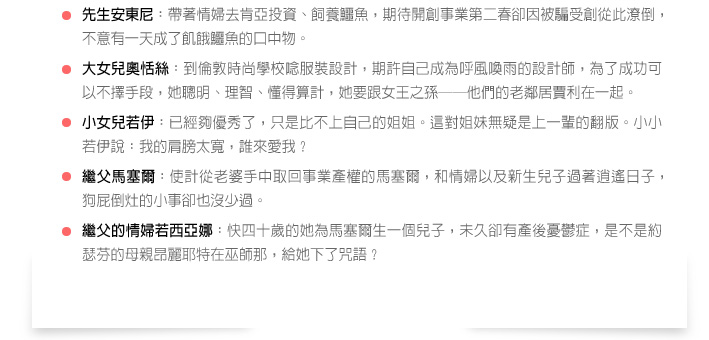

剩餘數量:4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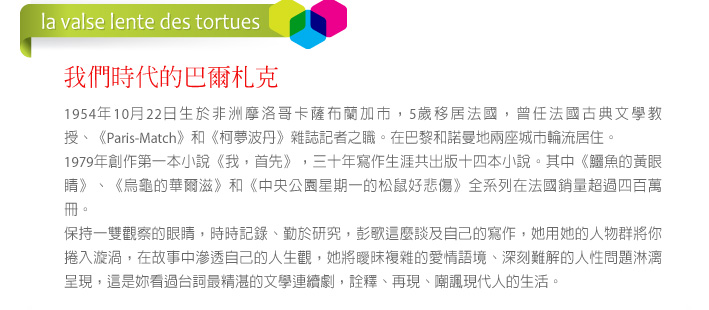





艾麗絲伸出手臂去抓鏡子。她的手在床頭櫃上摸索,但沒有找到。她坐起身,氣瘋了。有人偷了她的鏡子。一定是有人怕她打碎鏡子來割腕。他們把我當什麼了?一個把自己大卸八塊的傻子瘋子?為什麼我連了斷殘生的權利都沒有?他們為什麼連最後的自由都不給我?我這一生還有什麼指望!它已經完了,四十七歲半就完了。皺紋越來越深,皮膚越來越鬆弛,身上的贅肉越來越多。一開始這些贅肉還不明顯,藏著掖著,蓄勢以待。之後,一旦把你蠶食得差不多了,當你變成一副軟塌的皮囊,他們就一發不可收拾,毫不留情毀了你。我每天都可以注意到這一跡象。用我的小鏡子,查看膝蓋後面的皮膚,我留意那堆贅肉是不是伺機瘋長。天天躺在床上我可無法趕走那堆贅肉。我在這張床上日漸憔悴。我的臉色如同聖器室的蠟燭油一樣。我從醫生們的眼裏可以看到。別看我。別把我當成一個藥罐子一樣對我說話。我不再是一個女人,我成了實驗室的一個曲頸甑了。
她端起一個杯子,朝牆上砸去。
「我想看看我自己!」她大喊大叫,「我想看看我自己!把我的鏡子還給我。」
那是她最好的朋友,也是她最可怕的敵人。它映出她水汪汪、深邃的藍眼睛的變幻,或指出她的皺紋。有時候,把鏡子朝窗戶那邊轉過去,它就為她籠上一圈光環,讓她又顯得年輕了。把它朝牆這邊轉,它讓她陡然老了十歲。
「我的鏡子!」她一邊用拳頭捶打床單,一邊聲嘶力竭地叫喊。「我的鏡子,不然我就割斷自己的喉嚨。我沒有病,我沒有瘋,我只是被我妹妹出賣了。這種病你們是沒辦法醫治的。」
她抓住一支喝糖漿的湯匙,用床單擦拭乾淨,然後轉過來照自己。她只看見一張扭曲的臉,好像被一群蜜蜂叮咬過。她把勺子朝牆上丟過去。
到底發生了什麼?讓我孤身一人,沒有朋友,沒有老公,沒有孩子,與世隔絕?
而且,我是不是仍然存在?
當一個人孤獨的時候,他不再是任何人。想到嘉爾曼,她覺得並非如此,但她拒絕這麼去想,認為嘉爾曼根本就無足輕重,以前她一直喜歡我,以後她也會一直喜歡我。而且,她讓我心煩,嘉爾曼。忠誠讓我心煩,美德讓我感到壓抑,沉默讓我想要扯爛自己的耳朵。我想要聽到聲音,笑聲、香檳、粉色的燈罩、對我心儀的男人之目光、女友的流言蜚語。貝朗吉爾沒有來看過我。她心中有愧,因為在巴黎晚宴上當別人說我壞話時,她沉默不語,她沉默不語直到她再也憋不住,對著那群人大喊:「你們真刻薄,可憐的艾麗絲不該受到蹲醫院的懲罰,她只是太不小心了,」而其他人尖叫著打斷她的話:「不小心?妳真善良。妳想說的是不誠實吧!根本就是太不誠實了!」就這樣,掙脫了對朋友的忠誠枷鎖,她又津津有味地品嘗每一句話,任由自己陷入閒言碎語的泥淖:「的確她的所作所為不對。一點都不對!」回到了那群毒舌婦的陣營,每個人都用自己的方式,抹黑不在場的那一位。「她真是活該,」最惡毒的一個總結道,「她再也不能用她的輕蔑壓垮我們了,她已經什麼都不是了。」悼詞結束,該尋找新的獵物了。
她們沒有錯,艾麗絲承認,環顧白色的房間、白色床單、白色百葉窗。事實上我是誰?什麼人都不是。我不再有內容。我已經徹底毀了,我可以成為字典裏對「失敗」的定義。失敗,普通名詞,陽性,詳見艾麗絲·杜班。我最好還是恢復做女孩時的姓氏,我的婚姻不會持續太久了。約瑟芬會拿走我的一切。我的書,我的老公,我的兒子,我的錢。
人們能和家人、朋友、丈夫、兒子斷絕聯繫而活嗎?還有和過去的自己斷絕。我將成為一個魂魄。融化在虛無之中,發現自己從來就沒有過任何實質。發現自己從來都只是一個表象。
以前,我存在是因為別人都看著我,賦予我思想、天分、風格、優雅。以前,我存在是因為我是菲力普·杜班的妻子,我擁有菲力普·杜班的信用卡,菲力普·杜班的地址。大家怕我,敬重我,拍我的馬屁。我可以教訓貝朗吉爾,在母親面前大出風頭。我也曾經成功過。
她把頭向後一仰,發出一陣憤怒的笑聲。多麼可憐的不屬於妳的成功,自己不能親手打造、不能一塊石頭一塊石頭砌築起來的成功!當你失去它,你就只能去蹲街頭,伸手乞討了。
還在不久前,當艾麗絲還沒有生病,一天晚上她買完東西兩手拎著大包小包要回家的時候,她跑著去追一輛計程車,她碰到跪坐在地上的一個乞丐,垂著眼睛,彎著脖子。每掉一個硬幣在他的碗裏,他就啞著聲說,謝謝先生,謝謝夫人。這並不是她那晚遇到的第一個乞丐,但她不知道為什麼,他躍入了她的眼簾。她加快腳步,移開目光。沒有時間施捨他,計程車已經遠去,那天晚上,他們還要出去應酬,她得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,泡一個澡,從懸掛衣架上的幾十件衣服中挑一條裙子,梳頭,化妝。回去的時候,她還跟嘉爾曼說過,我才不要像街上那個乞丐那樣,對吧?我不想變成窮鬼。嘉爾曼發誓這種事情永遠不會發生在她身上,她哪怕做家務磨壞了手都要讓她繼續光采照人。她信了她。她把蜂蜜美容面膜擺好,滑入浴缸的熱水中,閉上眼。
可是,我現在的情形離一個女乞丐相去不遠,她一邊想一邊掀起床單找鏡子。鏡子可能滑落在床上。可能我忘了把它放回原處,它躲在床單的某個褶子裏。
我的鏡子,把我的鏡子還給我,我要看看我自己,確信自己存在,確信自己沒有從人間蒸發。我多麼希望還可以取悅他人。
每晚給她吃的藥生了效,她又發了會兒譫妄,看見父親坐在她的床尾看報紙,母親在檢查她帽上的別針是否都卡牢了,菲力普領著穿白紗的她走過教堂中間的長長甬道。我從來沒有愛過他。我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人,我只希望別人愛我。可憐的姑娘!妳真令人同情。有朝一日,我的王子會來,有朝一日我的王子會來……嘉波。他是我迷人的白馬王子。嘉波·米納爾。聞名全球的大導演,他的名字光芒四射,大家都想乖乖地蜷縮在他的聚光燈下。為了他我可以拋下一切:丈夫、孩子、巴黎。嘉波·米納爾。她吐出他的名字,彷彿是一種責怪。當他一窮二白、沒有成名的時候,我不愛他,當他出名了,我對他心醉神迷。我總喜歡受人注目。哪怕是愛情。我是個多麼勢利的愛人啊!
艾麗絲是清醒的,這更加深了她的不幸。有時候她氣糊塗了的時候會變得很不公允,但很快她就恢復了理智,咒罵起自己。罵自己懦弱,罵自己膚淺。我一出生命運就給了我一切,但我卻無所作為。我任由自己隨波逐流。
如果她稍微有一點自尊自強,再加上這點有時把自己看得過低的無情的清醒,她本可以自我改進,開始善待自己。自尊,不是嘴上說說這麼容易。它需要努力,需要用功,光想到這個念頭,她就厭惡地皺起鼻子。而且,她注意到,自己已經沒有時間了。人生在四十七歲半上不可能重頭再來了。可以補補綴綴,可以亡羊補牢,但不可能整飭一新了。
不,她對自己說,感到睡意向她襲來,她硬撐著想找到一個出路,我必須趕緊,趕緊找一個新老公。比菲力普更有錢,更強大,更重要。一個非常強勢的老公。讓我仰慕,讓我傾倒,讓我像一個小姑娘一樣拜倒在他的跟前。他會把我的命運握在手裏,重新把我放在世界的某一個位置上。用錢、關係和筵宴。我風韻猶存。一旦從這裏出去,我就會又變成美麗、無與倫比的艾麗絲了。
這是我被關在這裏以來第一次有這麼積極的想法,她一邊呢喃,一邊把床單拉到下巴下,或許我正在康復?
***
當愛情在心上穿了一個洞,一個大洞,大得彷如炸彈炸開似,大得可以透過它看見天空,我們該怎麼辦?在去找呂卡的路上,約瑟芬邊走邊想。誰能告訴我他對我的感覺如何?我不敢對他說「我愛您」,我怕這句話太重了。我知道我的「我愛您」言下之意是我不敢說出口的「您愛我嗎?」怕他會把手從帶風帽的粗呢大衣口袋裏拿開。戀愛中的女人一定是患得患失、焦慮痛苦的女人嗎?
他在遊船附近等著,坐在一張長凳上,他的手插在口袋裏,伸直了腿,低頭大鼻子對著地面,一綹褐髮遮住了他的臉。她停下來,在走向他之前好好地看了他一下。不幸的是,我不知道怎樣在戀愛中表現得輕鬆自在。我想撲到愛人懷裏抱住他的脖子,但是我怕嚇到他,所以只謙卑地抬起臉龐接受他的親吻。我暗戀他。當他抬頭看我,當他捕捉到我的目光,我就和他聲息與共。我做他所希望的戀人。遠遠地為他狂熱,當他一靠近時就克制自己。您不知道這個,呂卡·賈姆貝利,您以為我是膽怯的老鼠,但是,如果您把手放在我內心燃燒的愛情火焰上,您勢必要被燒成重傷。我喜歡這個角色:讓您歡笑,讓您平靜,讓您迷醉,我把自己變成溫柔耐心的護士,把您願意給我的麵包屑改造成厚實的麵包片。我們見面約會已經一年了,我對您的了解並不比您在第一次約會時在我耳邊輕聲說的更多。在愛情裏,您像一個胃口不佳的男人。
他看到她了。他站起身,在她臉頰輕吻一下,幾乎是友愛的一個吻。約瑟芬改了主意,已經感到從這個輕描淡寫的親吻中生出的隱隱痛苦。今天,我要跟他好好談談,她決心拿出靦腆者的勇氣。我要把我的不幸一樁樁說給他聽。戀人是幹嘛用的,如果還要向他隱瞞自己的苦痛和不安?
「約瑟芬,您還好嗎?」
「原本可以更好一點……」
來吧,她告訴自己,勇敢點,做妳自己,告訴他,把受攻擊的事說給他聽,把明信片的事說給他聽。
「這兩天真可怕,」他繼續說道,「我弟弟周五下午失蹤了,就在我們約在我不喜歡但您很喜歡的酒吧間那天。」
他朝她轉過身,露出自嘲的笑容。
「他跟幫他治療狂躁症的醫生有約,之後就不知去向。我們四處找,直到今天早上他才露面。他情況很糟,我已做好最壞的打算。很抱歉放了您鴿子。」
他抓起約瑟芬的手,約瑟芬接觸到他細長、溫熱、乾燥的手,有些心慌意亂。她把臉貼在他粗呢大衣的袖口上,輕輕磨蹭著,彷彿在說不要緊,我原諒您。
「我等您等了一會兒,之後回去和若伊共進晚餐。我告訴自己,您一定碰到麻煩事了……呃……因為維托里奧。」
叫一個她不認識而且討厭她的男人之名,讓她感覺怪怪的。這讓她心裏直犯嘀咕。他為什麼討厭我呢?我又沒招惹他一根寒毛。
「他早上回家時,我正在等他。昨天一整天、一整夜我都在等他,坐在他家的長沙發上。他回來看了看我,好像不認識我一樣,精神恍惚,他衝到蓮蓬頭下,沒有鬆口說半句話。我說服他吃一片安眠藥,然後睡一覺,他連站都站不住了。」
他的手猛地握緊約瑟芬的手,好像要讓她知道這兩天他所受的等待,以及擔驚受怕的煎熬。
「維托里奧讓我擔心,我不知道怎麼辦。」
兩個正在慢跑的年輕苗條女人,在他們身邊停下來,她們手叉腰,喘著氣,看看錶,算一算還要再跑多久。兩人中間的一個上氣不接下氣地說:
「然後我告訴他:你到底想要怎樣?他對我說,妳知道他竟敢對我說,妳別逼我!我逼他?我告訴妳,我想我要結束了。我再也受不了他了。還有什麼?做取悅他的藝伎?讓他騎在我頭上?為他準備美味小菜,當他一聲令下就張開雙腿?還不如一個人生活。至少我可以清靜清靜,還少點事!」
年輕女人把手臂抱在胸前,彷彿鐵了心,她細長的褐色眼睛閃著怒火。她的女友吸吸鼻子表示贊成。然後示意她繼續跑步。
呂卡看著她們遠去。
「看來有麻煩的人還不單單只有我一個!」
是說出妳悲慘遭遇的時候了,說吧,約瑟芬給自己打氣。
「我也是……我也遇到麻煩了。」
呂卡挑了一下驚訝的眉毛。
「我遇到一件非常不愉快的事和一件很奇怪的事,」芬盡量平靜地說道。「我先說哪一件?」
一頭黑色的拉布拉多犬飛快地從他們跟前跑過,跳進水裏。呂卡轉移了注意力,看牠跳到綠乎乎的湖水裏。水面一層油污,蕩開一圈圈彩虹色漣漪。張著大嘴,那隻狗一邊游一邊喘氣,牠奮力游著,以叼回主人扔去的一個球。牠黑色的毛皮閃閃發光,掛著一顆顆水珠,在牠身後留下了一道道水紋;野鴨慌忙避讓,在稍遠處休憩,小心提防著。
「這些狗真不可思議!」呂卡感歎道,「您看!」
那條狗回來了,牠抖抖身上的水,把球放在主人腳邊,搖著尾巴,汪汪叫,希望遊戲可以繼續。我該怎麼接下去說?約瑟芬暗自思忖,目光跟著又被丟出的皮球和跳入水中的狗。
「剛才您說什麼,約瑟芬?」
「我說我遇到兩件事,一件很暴力,一件很奇怪。」
她勉強笑了笑,好讓自己的訴說輕鬆一點。
「我收到一張安東尼的卡片……呃……您知道,我先生……」
「可是我以為他已經……」
他不敢說出那個詞,約瑟芬替他說了:
「死了?」
「是的。您說過……」
「我也以為他死了。」
「這很奇怪,的確。」
約瑟芬等著他提問,或提出一個假設、驚叫,好歹對這個消息有點反應,但他只是皺了皺眉頭,接著問:
「那另一個呢,那個暴力的?」
什麼?約瑟芬心想,我告訴他一個死人寫明信片,買郵票貼在卡片上,再把信投到郵箱裏,他卻對我說:「還有什麼別的事嗎?」在他看來這很正常。死人夜裏起來寫信。而且,死人並沒有死,他們在郵局排隊,正因為如此,在郵局才老是等個沒完。她嚥了一下口水,不假思索地說出來:
「我差一點被人謀殺!」
「謀殺,您?約瑟芬?這不可能!」
為什麼不?或許是我死了也只是小事一樁,因為我不是重要人物?
「周五晚上,我們沒約成,在回家路上,有人拿匕首刺我的胸口。就在這裏!」
她拍了拍胸口,為了加強這句話的悲劇色彩,卻感到自己可笑。說自己是社會事件的受害者完全不具可信度。他一定認為我在編故事以和他弟弟一爭高下。
「您的故事,根本就站不住腳!如果您被匕首刺中心臟,早就死了……」
「一隻鞋子救了我的命。安東尼的鞋子……」
她平靜地解釋來龍去脈。他一邊聽她說,一邊看著群鴿飛翔。
「您報警了?」
「沒有。我不想要若伊知道。」
他狐疑地看著她。
「這怎麼行,約瑟芬!如果您路遇歹徒,就應該報警。」
「為什麼說『如果』?我是真的遇到了。」
「想想看,如果這名男子又加害他人,您會自責的。死去的人會讓您良心不安。」
他不僅沒有把她摟在懷裏安慰她,不僅沒有對她說「我在這裏,我會保護您」,還在這裏怪罪她,想著下一個可能的受害者。她無奈地朝他一瞥,這一個男人,該怎麼做才能讓他動容?
「您不相信我?」
「不是……我相信您。我只是建議您去報案。」
「您好像很懂這一套!」
「有這麼一個弟弟,警察局我是識途老馬了。幾乎所有巴黎警察局我都認識。」
她盯著他,神情愕然。他又回到自己的事情上,他只是拐一個彎聽她說了點兒話,重又把自己封閉在自身的不幸裏。這就是我的戀人,我心儀的男人?那個正在寫一部關於眼淚的書的男人,還引用米什萊(Jules
Michelet)的話:「珍貴的眼淚,它流淌在清澈的神話裏,流淌在美妙的詩歌裏,朝著天空的方向彙聚,凝結成恢弘的大教堂,迎向天主」。一顆冷酷的心,是的。一顆科林斯(Corinthe)葡萄。他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,將她拉到自己身邊,用溫柔而倦怠的聲音囁嚅道:
「約瑟芬,我不能管所有人的煩心事。放輕鬆,好嗎?和您在一起我很自在。您是我快樂、歡笑、柔情的惟一所在。請您,不要破壞它……」
約瑟芬乖乖點點頭。
他們繼續在湖邊散步,遇到其他跑步者,游泳的狗,騎自行車的孩子,跟在孩子後的他爸爸,弓著背,扶著孩子的車,一個身材魁梧的黑人裸著上身,跑得渾身是汗。她本想問他:「我們約在酒吧那晚,您打算告訴我什麼?好像頗重要的樣子」,但她打消了念頭。
呂卡的手搭在她肩上,撫摸著,但她隱約覺得,那隻手想逃走。
就在那一天,她貼在呂卡身上的心撕開了一小塊兒。